在现代文阅读中,作者生平对文本解读的影响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通过综合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学及具体案例分析,可从以下角度探析其作用与局限:
一、作者生平对文本解读的积极意义
1. 还原创作语境,深化主题理解
作者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与其创作动机紧密相关。例如,金立义在分析《番茄太阳》时指出,了解作者卫宣利因车祸致残的经历后,才能更深刻理解文本中盲童明明的乐观如何成为作者情感救赎的象征。这种“知人论世”的方法(孟子提出)帮助读者建立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避免孤立解读。
2. 捕捉隐含意图,消解文本歧义
作者的生平资料常为文本中的隐喻、象征提供注解。如杰克·伦敦的《海狼》曾被误读为宣扬尼采超人哲学,但结合其童年童工经历,可发现文本实为对贫困与人性异化的批判。赵炎秋强调,作者意图始终在场,文本的语言结构和细节往往暗含其思想倾向。
3. 补充文本空白,丰富人物塑造
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常折射作者的价值观或情感态度。例如,《詹天佑》中主人公的爱国担当,需结合清末列强侵华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民族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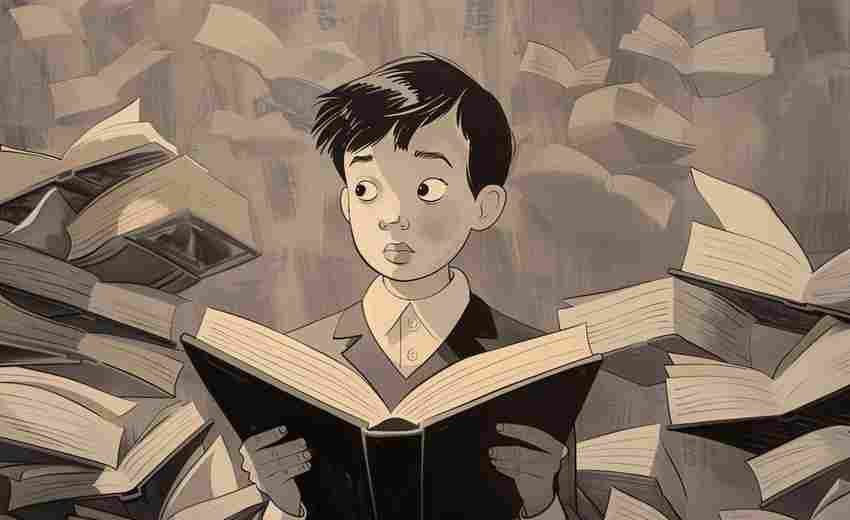
二、过度依赖作者生平的局限性
1. “意图谬误”的批判:文本的独立性
新批评派(如维姆萨特)提出“意图谬误”,认为文本一旦完成便脱离作者控制,其意义由语言自身构建。例如,曹禺创作《雷雨》时并未预设明确的哲学主题,但文本的复杂人性与命运悲剧远超作者原意。若仅以作者生平为唯一解读依据,可能忽视文本的多义性。
2. 读者主体性的崛起与接受美学的挑战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如费希、尧斯)强调,文本意义由读者与文本互动生成。例如,狄更斯隐瞒童年经历,但读者仍能从《大卫·科波菲尔》中独立解读社会批判。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进一步指出,读者与作者的历史视界交汇形成新的理解,作者意图无法垄断阐释权。
3. 形象大于思想:文本的自我生长性
歌德曾表示,《浮士德》的意义无法被单一观念概括,因为文学形象具有独立生命。杰克·伦敦虽意图批判超人哲学,但拉森形象的强大仍被解读为超人哲学的印证,说明文本可能“背叛”作者意图。
三、平衡作者生平与文本自足性的路径
1. 以文本为中心的“合理游走”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活动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的互动模型。现代批评应“以作品为核心”,兼顾作者意图与读者阐释,如罗伯特·尧斯将接受美学转化为“文学交流理论”,强调作者、文本、读者的辩证关系。
2. 区分“原典意义”与“解释意义”
赫斯(E.D. Hirsch)将文本意义分为“作者原意”(meaning)与“读者赋予的意味”(significance)。作者生平有助于挖掘原典意义,而读者的社会语境则生成多元解释。例如,《厄运打不垮的信念》的主题需结合谈迁生平,但其励志价值可被不同时代读者重构。
3. 结合多重证据的综合性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流派主张将文本置于社会网络中考量。例如,分析鲁迅作品时,需综合其个人经历(如弃医从文)、民国社会思潮及读者接受史,避免单一维度的片面解读。
作者生平为文本解读提供了重要语境,但绝非唯一依据。现代文阅读需在“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之间动态平衡,既尊重创作原意,又承认文本的开放性与读者的主体性。正如金立义所言,教师解读应“从作者立场出发”但不拘泥,最终回归文本的“原生价值”与“教学价值”。这种多维度的批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文学阐释的深度与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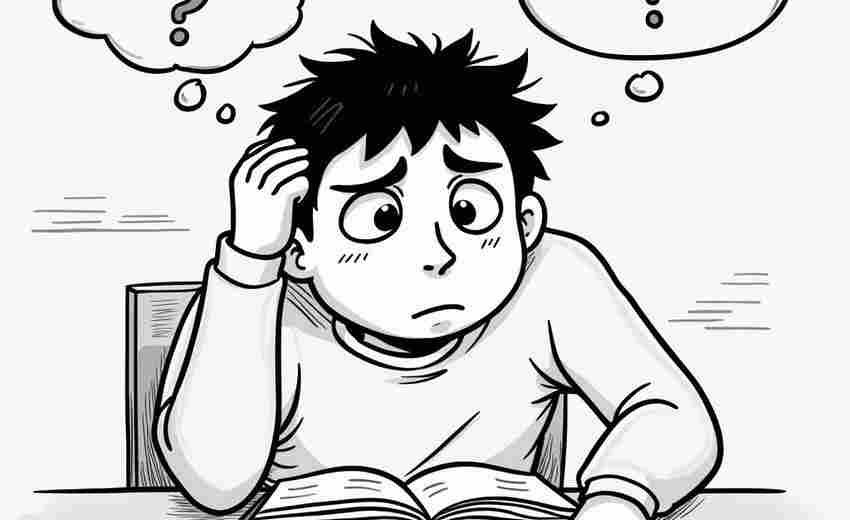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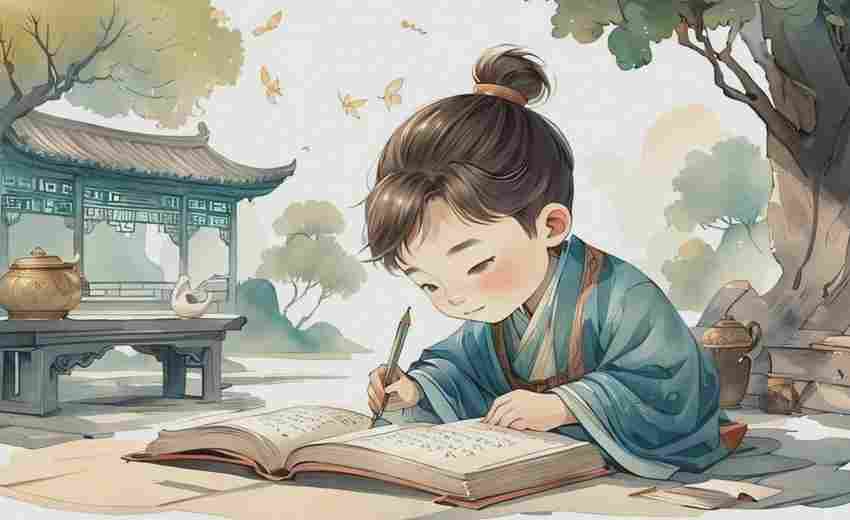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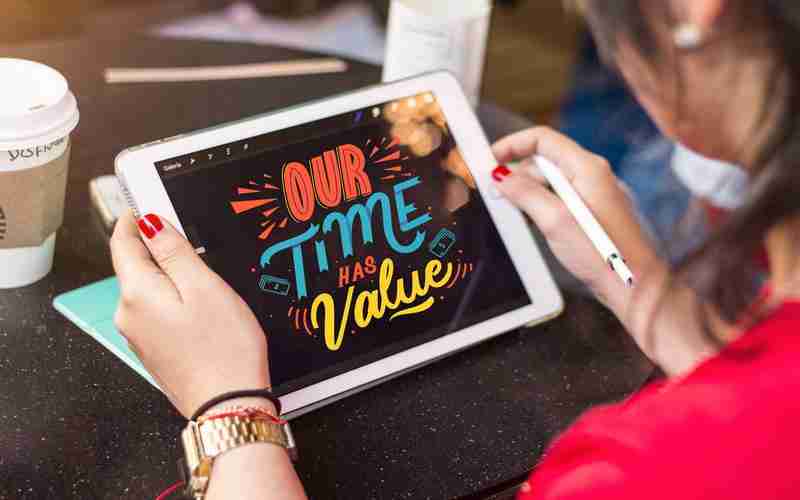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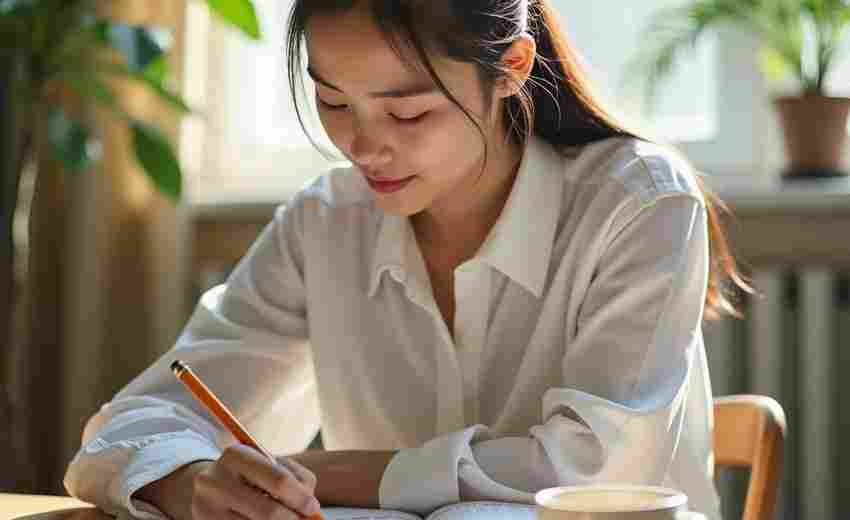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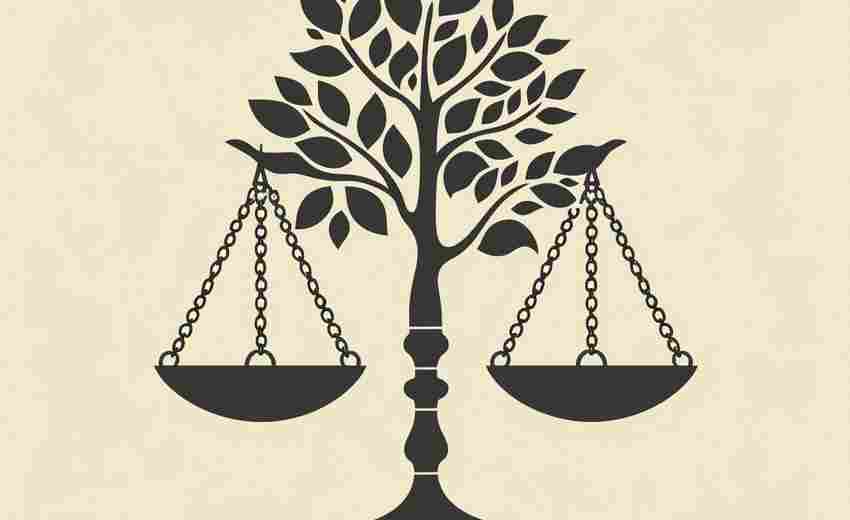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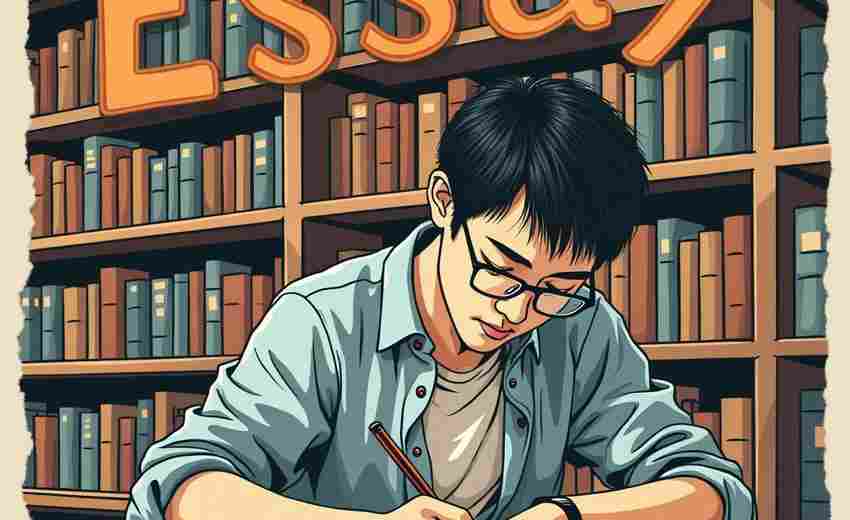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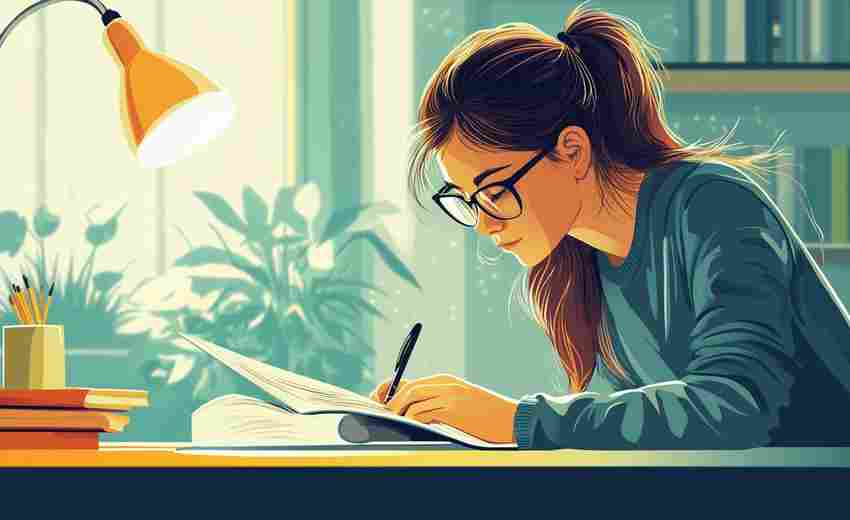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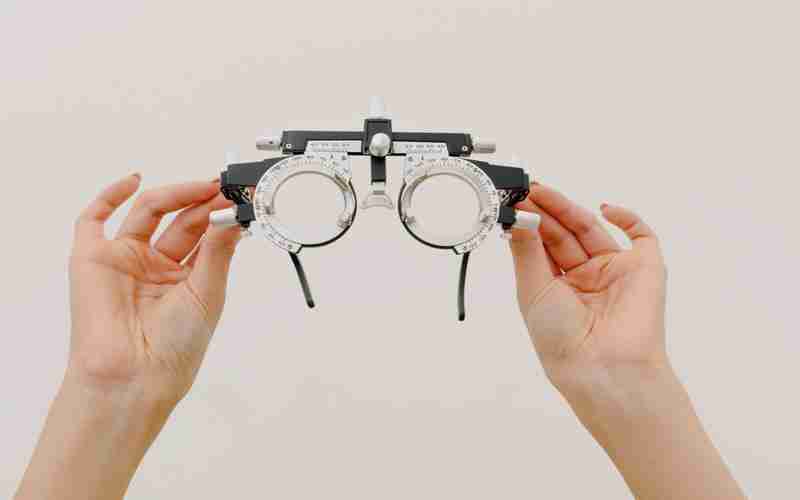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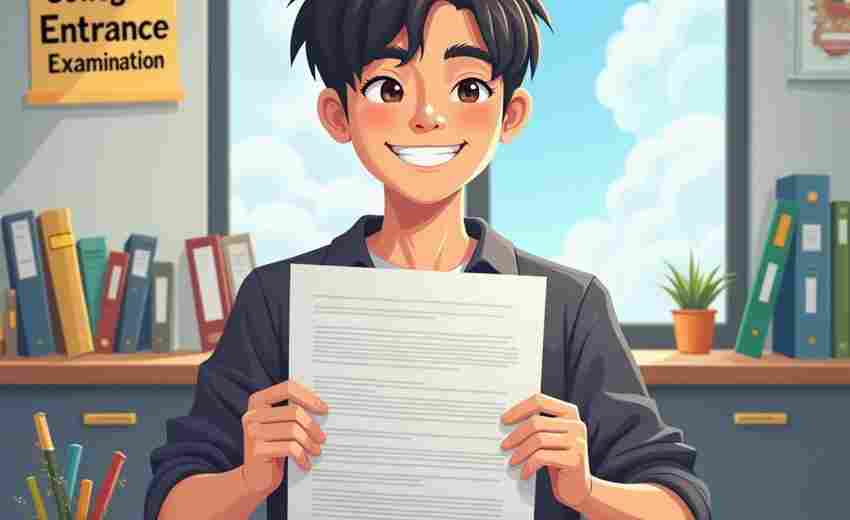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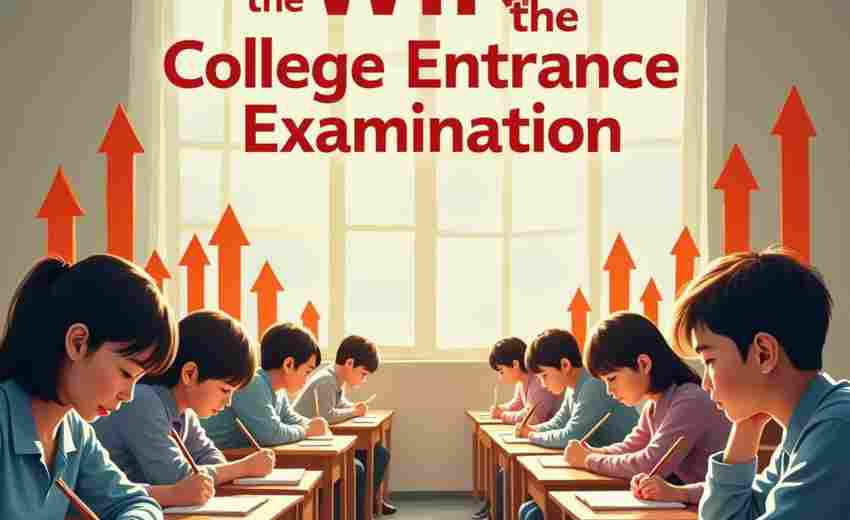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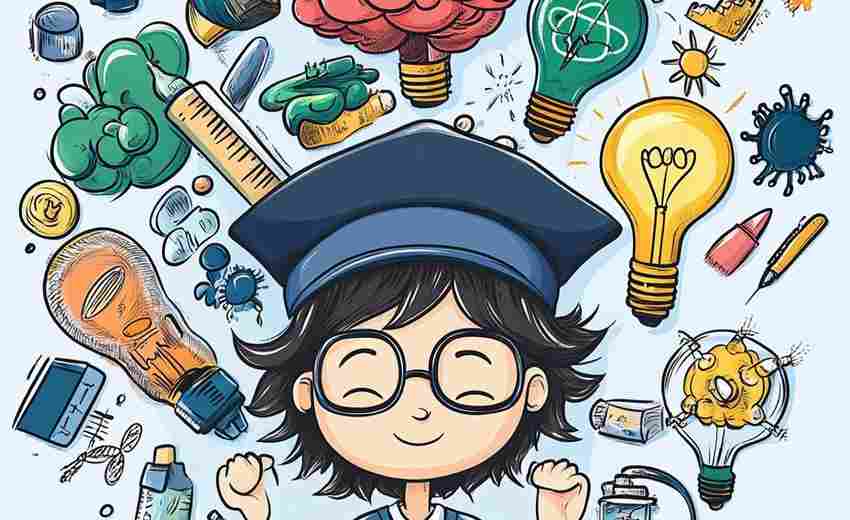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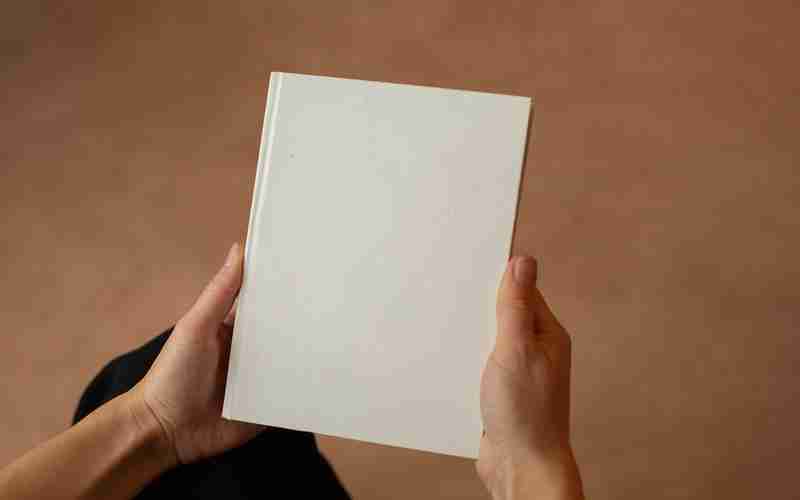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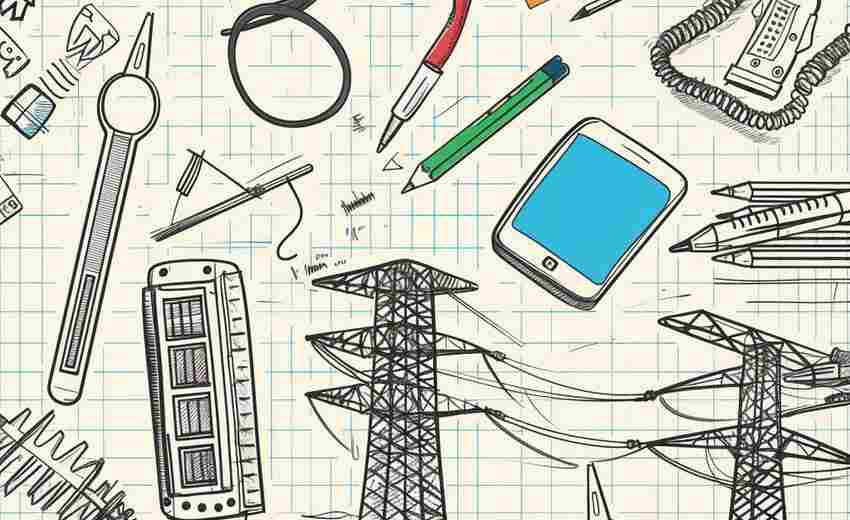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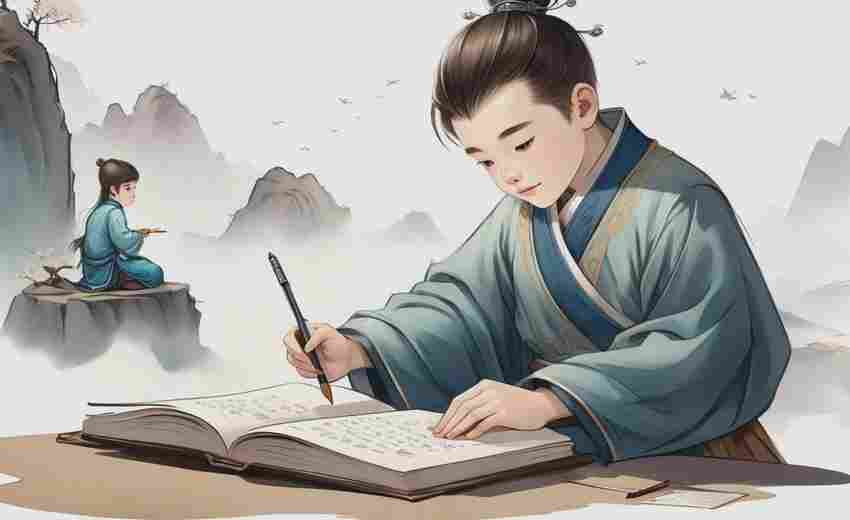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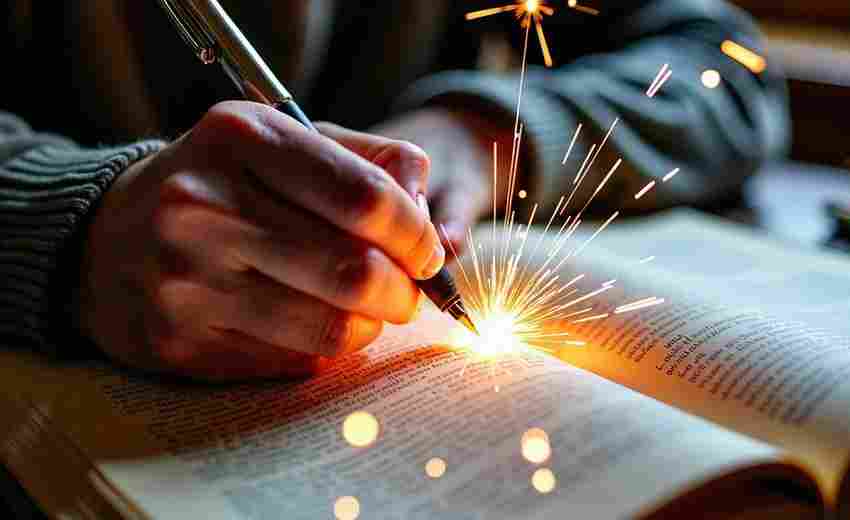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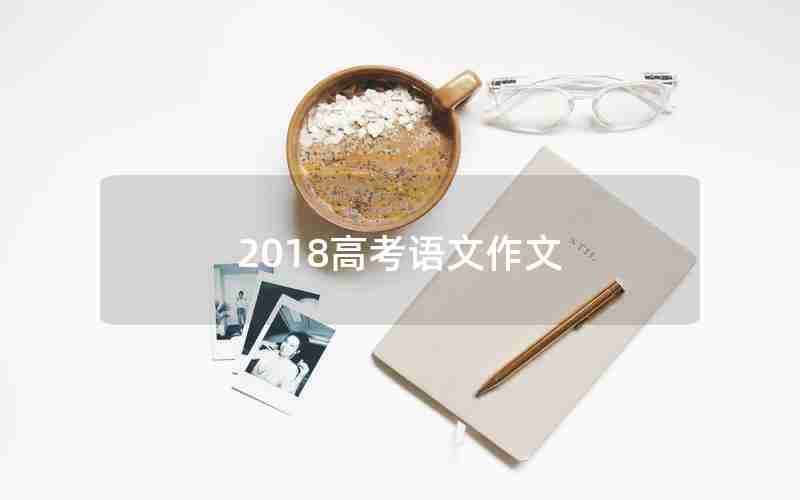

推荐文章
影响分数线的社会因素有哪些
2024-11-01高考志愿填报中,如何防范信息不对称
2024-11-16浙江省艺术大学设计专业的学科特点是什么
2024-11-28西北师范大学师资规模是否满足高考生多元化学习需求
2025-05-11高考志愿填报的地理位置重要吗
2024-12-14高考体育特长生需了解哪些体育教育专业理论课程
2025-03-19如何应对专业不喜欢的情况
2025-01-05航空航天工程的就业前景如何
2024-12-01海南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学术资源
2024-12-27广播电视编导与新闻传播学的高考选科要求有何差异
202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