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中,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作用不仅是简单的视角选择,更是一种融合情感表达、主题深化与结构设计的艺术手段。以下结合高考真题与文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其独特作用:
一、真实性与代入感的双重强化
1. 增强叙述的真实性
第一人称通过“我”的亲历性视角,使读者产生“见证者”的信任感。例如《古渡头》中,“我”作为旁观者倾听渡夫自述人生,既保留了故事的真实性,又通过对话形式让渡夫的悲剧更具感染力。这种视角的有限性(仅呈现“我”所见所闻)反而强化了叙事的可信度。
2. 拉近读者距离
“我”的参与使读者更容易代入情感。如《孔乙己》中,儿童视角的“我”冷静观察掌柜与孔乙己的互动,既呈现了天真的叙述口吻,又隐含对社会荒诞的批判,读者在“天真”与“残酷”的对比中感受主题深度。
二、心理描写与情感抒发的直接性
1. 细腻的心理刻画
第一人称便于直接展现人物内心活动。例如《祝福》中“我”面对祥林嫂追问时的矛盾心理,既暴露知识分子的软弱,又深化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主题。这种心理描写使情感表达更具冲击力。
2. 情感共鸣与主题引导
“我”的抒情性叙述能直接引发读者共情。如《呼兰河传》中,儿童视角的“我”回忆祖父与后花园的温暖时光,与成人视角的冷峻现实形成对比,既凸显童年美好,又暗含对旧社会麻木的批判。
三、视角限制带来的艺术效果
1. 悬念与留白
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常通过遮蔽信息制造悬念。例如《鲤鱼巷》中,老柳的内心独白仅通过“我”的旁观视角片段式呈现,其忧伤与怀念需读者自行拼凑,增强了文本的含蓄美。
2. 多重视角的转换
高考文本常通过“双重视角”拓展叙事层次。如《冬阳·童年·骆驼队》中,前半部分以儿童视角展现天真好奇,结尾转为成人视角追忆往昔,时空交叠深化对童年消逝的感慨。
四、作为结构线索与主题载体的功能
1. 串联情节的线索作用
“我”的观察与经历常构成文本主线。例如《古渡头》以“我”与渡夫的偶遇为框架,通过对话推动情节,使叙事紧凑集中。
2. 深化主题的隐喻性
第一人称叙事者本身可能具有象征意义。如《新生》中以“死去孩子”的视角叙述战争创伤,其虚拟视角既控诉战争罪恶,又通过“灵魂”的游离状态隐喻人性的异化。
五、儿童视角的特殊性
在高考文本中,儿童视角的“我”常被赋予独特功能:
高考命题中的考查重点
高考常围绕以下角度设题:
1. 真实性效果:如《古渡头》中“我”的见证者作用。
2. 心理与情感表达:如《祝福》中“我”的内心矛盾对主题的深化。
3. 视角转换与结构设计:如《冬阳·童年·骆驼队》的双重视角对比。
4. 儿童视角的象征意义:如《呼兰河传》中温暖与冷酷的并置。
考生需结合具体文本,从叙述者身份、情感层次、结构功能等维度综合分析,方能全面把握第一人称的独特艺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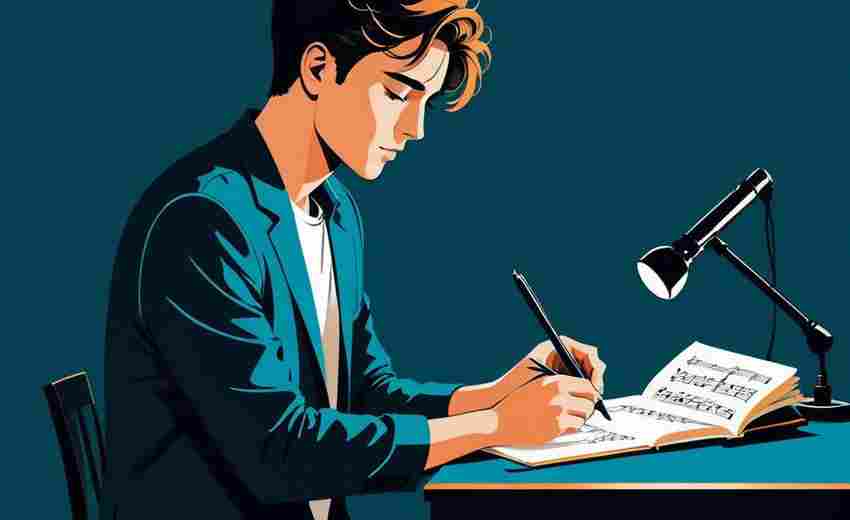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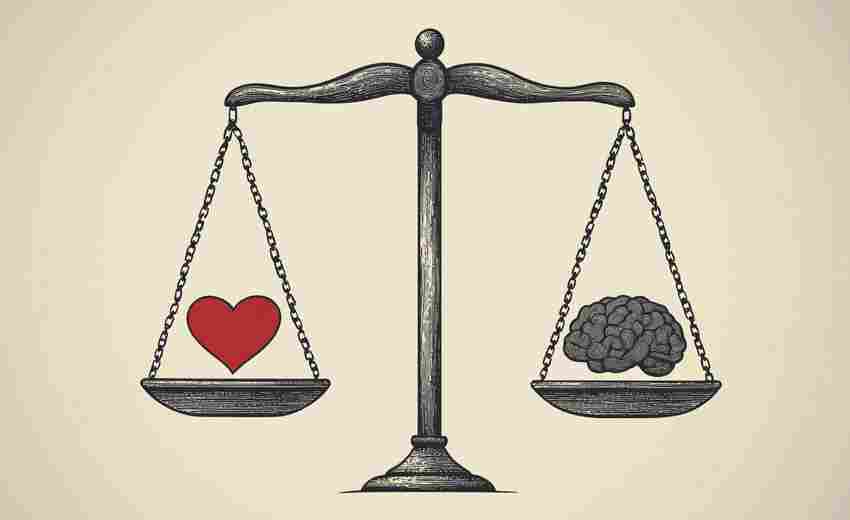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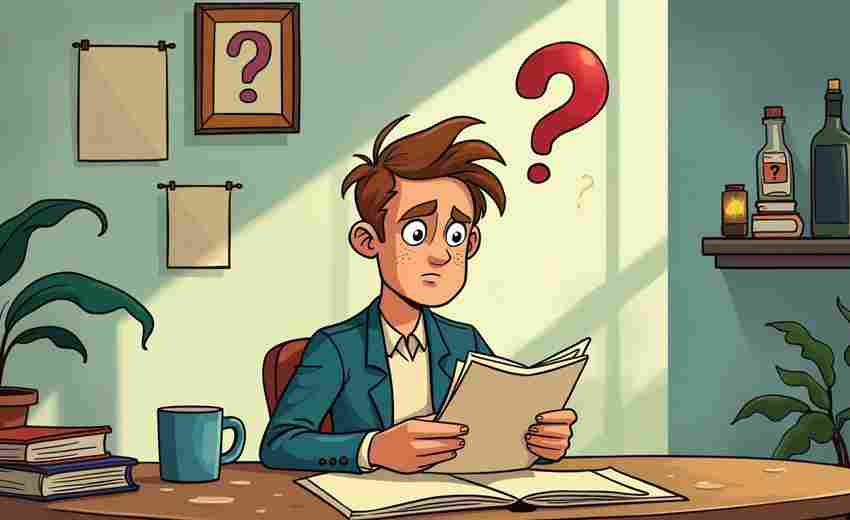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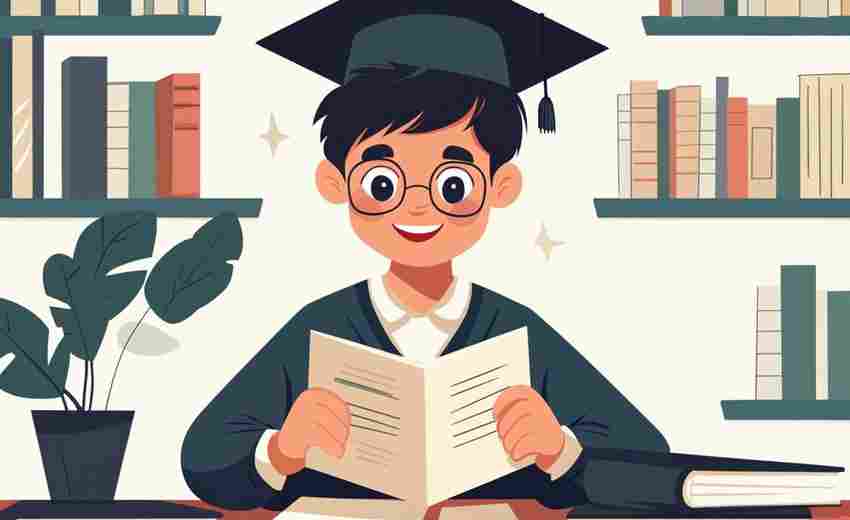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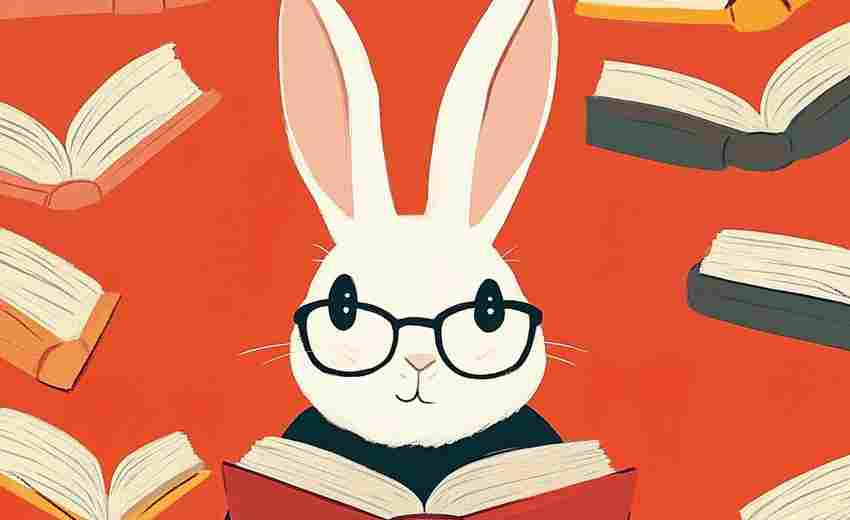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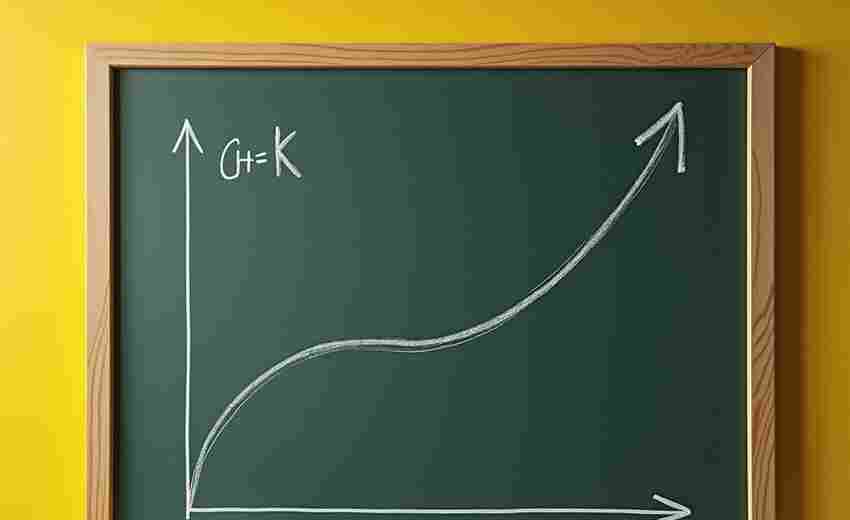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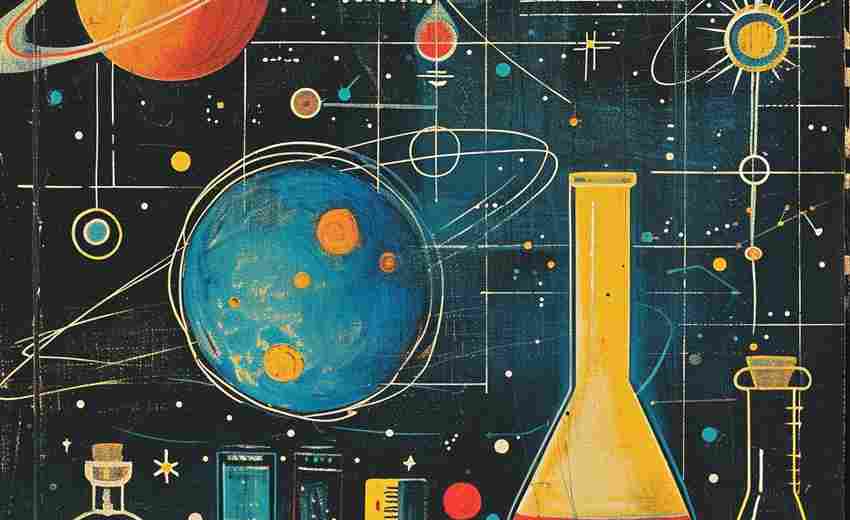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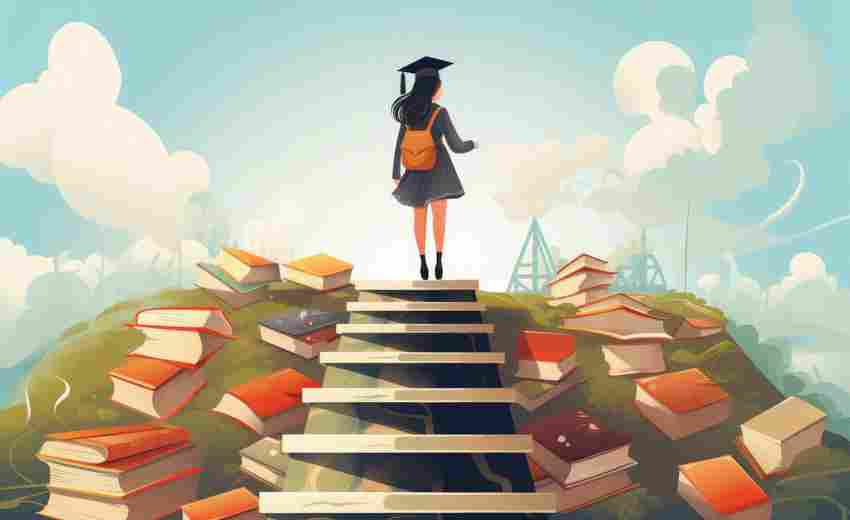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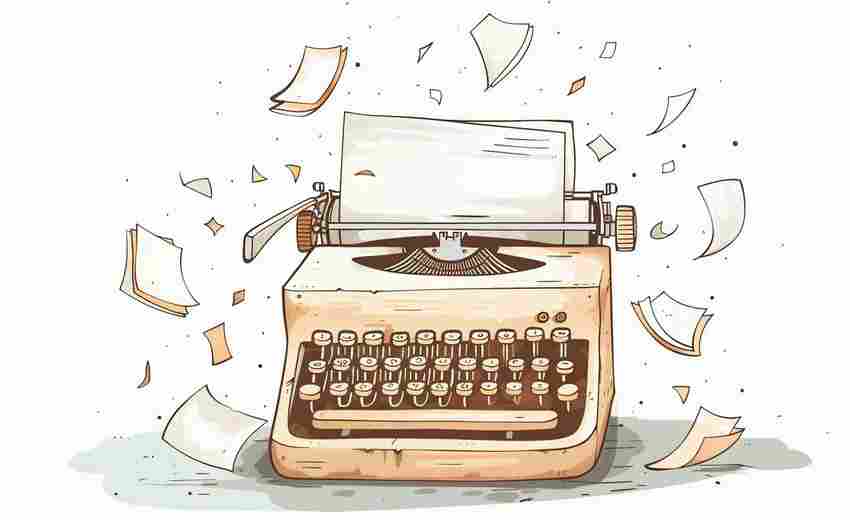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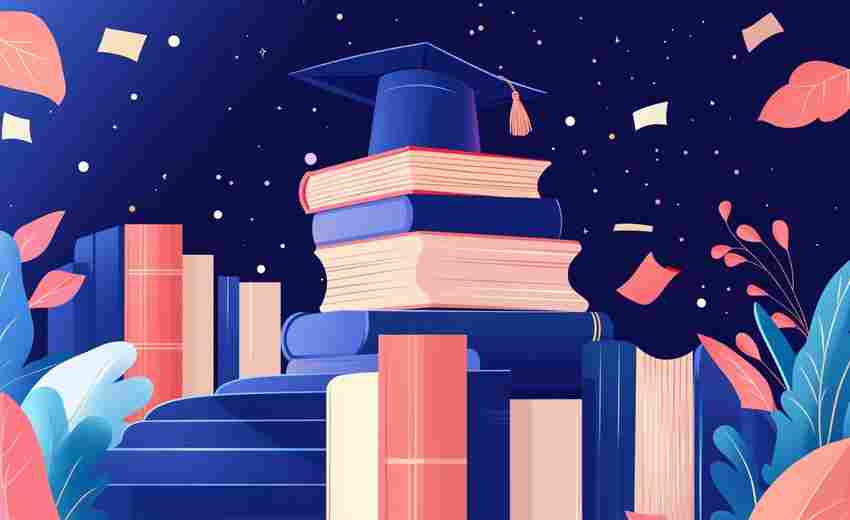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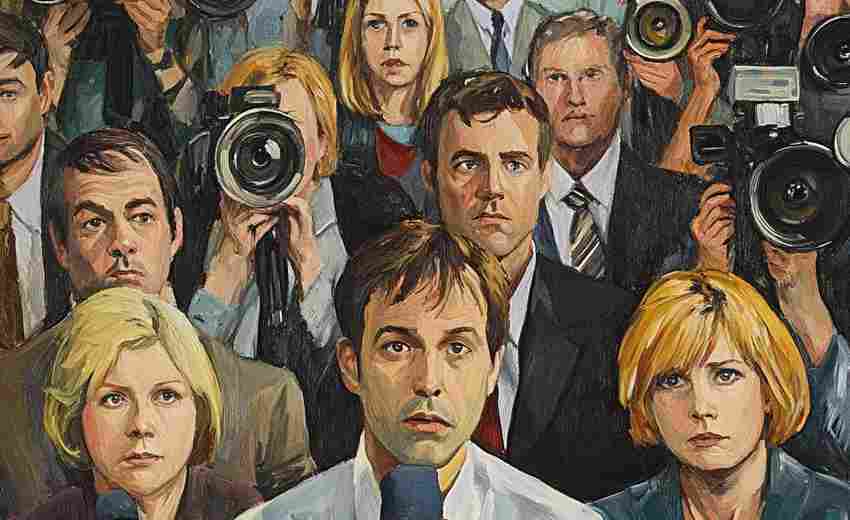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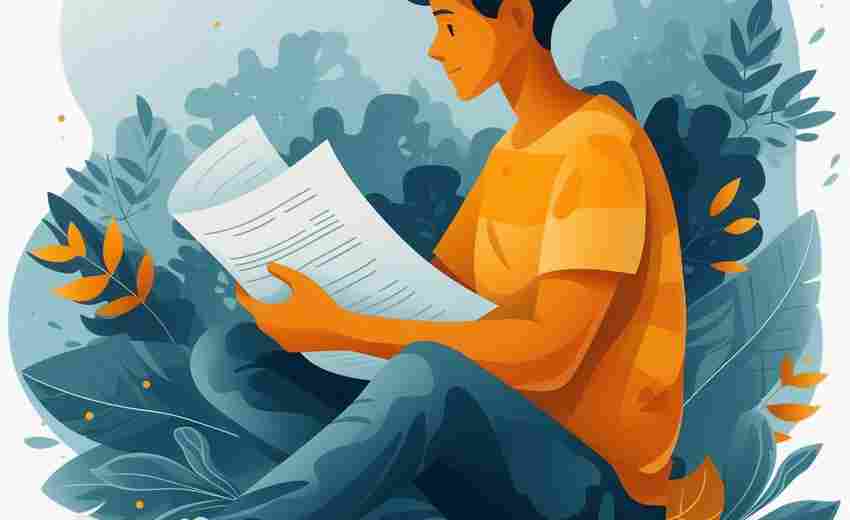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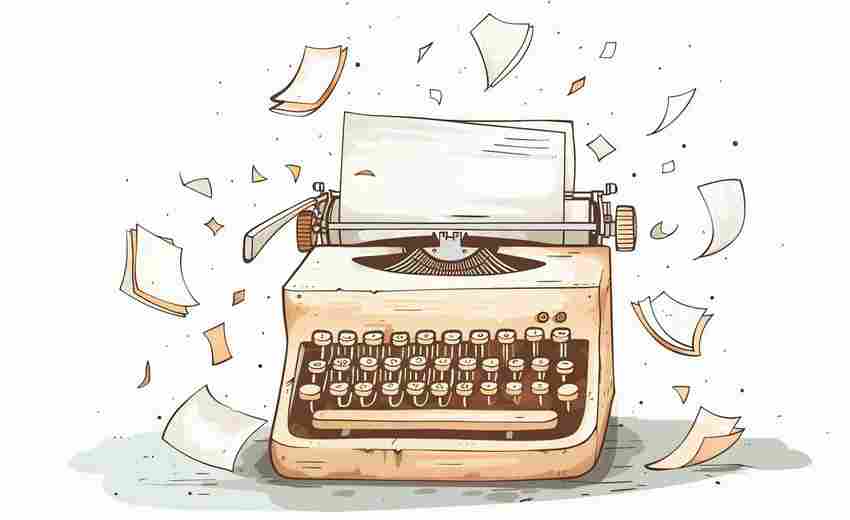


推荐文章
高考志愿填报时,如何选择学科方向
2024-11-25影视编导专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2025-01-30动漫与游戏设计的职业发展路径
2024-12-15理科综合与文科综合的区别
2024-12-21专业和职业发展的关系
2024-12-10文史类专业有哪些推荐
2024-10-26如何了解太原大学的教师资源
2025-01-01高校专业的热门与冷门如何判断
2025-01-19高考法律专业报考必备的十大基础法律概念解析
2025-03-26传媒专业和新闻专业有什么不同
2025-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