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教育差异导致的高考分数线“梯度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现象,涉及教育资源分配、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招生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下从不同维度解析其形成机制及具体表现:
一、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
1.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化
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拥有更多重点高校和优质师资,例如北京集中了全国近半数教育部直属高校,本地考生可享受更高的“属地招生比例”(部分高校本地招生占比达3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如河南、贵州)高校数量少且质量较低,导致考生需通过更高分数竞争有限的优质名额。
2. 教育投入的区域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生均教育经费显著高于欠发达地区。例如,2023年上海生均教育经费是甘肃的3倍以上,这使得东部学生在教学设施、课外辅导等方面更具优势,间接推高了其整体成绩水平。
二、招生政策的“结构性倾斜”
1. 分省定额与名额投放
高校招生计划遵循“属地优先”原则,如青海大学68%的招生名额分配给本地,西藏大学本地录取率高达50%以上。而经济发达省份通过财政支持高校建设换取更多招生指标(如某顶尖高校曾承诺“为宿舍建设省份降10分录取”)。
2. 政策补偿的局限性
尽管国家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但优质高校(如985/211)的招生名额仍向东部倾斜。例如,北京考生进入清华、北大的概率是河南考生的30倍,导致中西部省份考生需通过更高分数竞争同一层次的院校。
三、人口与竞争的“双向挤压”
1. 考生基数与录取率的矛盾
河南、广东等人口大省考生数量庞大(2024年河南考生超130万),但本地优质高校资源匮乏,导致“一本上线率”仅为北京的1/3,分数线被迫抬升以筛选考生。
2. “高考移民”与政策博弈
部分考生通过迁移户籍至分数线较低的省份(如黑龙江、青海)获取升学优势,进一步加剧本地竞争,迫使这些省份调整政策限制移民,形成分数线波动。
四、历史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1. 科举制度的现代延续
从元代“分省取中”到清代“南北卷制度”,中国历史上长期通过配额制平衡区域差异。现代高考的分省定额录取模式直接承袭了这一传统,旨在缓解区域间教育水平差异,但也固化了分数线差异的合法性。
2. 自主命题与评分标准差异
北京、上海等地采用自主命题,试卷难度和评分标准与其他省份不同,导致横向比较失效。例如,山东与北京曾共用同一试卷时,山东一本线高出北京120分,促使北京此后改用独立命题。
五、经济与社会的“隐性杠杆”
1. 家庭资本的影响
发达地区家庭更易通过课外培训、竞赛加分等途径提升竞争力。例如,上海考生参与学科竞赛并获得加分的比例是西部省份的5倍以上,间接降低了实际录取分数线。
2. 就业市场与教育期望
东部地区高学历就业机会多,家长对教育的投入意愿更强,形成“高投入—高成绩—低分数线”的循环。而中西部地区部分家庭因经济压力更倾向于职业教育,降低了高考竞争强度。
六、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
1. 动态调整招生配额
按人口比例和基础教育质量综合分配名额,例如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试点按各省人口比例招生,但因阻力未能推广。
2. 强化跨区域教育资源均衡
通过“双一流”高校异地校区建设(如哈工大深圳校区)、中西部高校专项支持计划等,逐步缩小区域差距。
3. 完善综合评价体系
借鉴浙江“三位一体”模式,将高考成绩与综合素质评价结合,减少单一分数对录取的决定性作用。
区域教育差异导致的分数线“梯度差”本质上是教育资源、政策设计、经济水平与人口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短期内,分省定额制度仍是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折中选择;长期则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推动从“机会公平”向“质量公平”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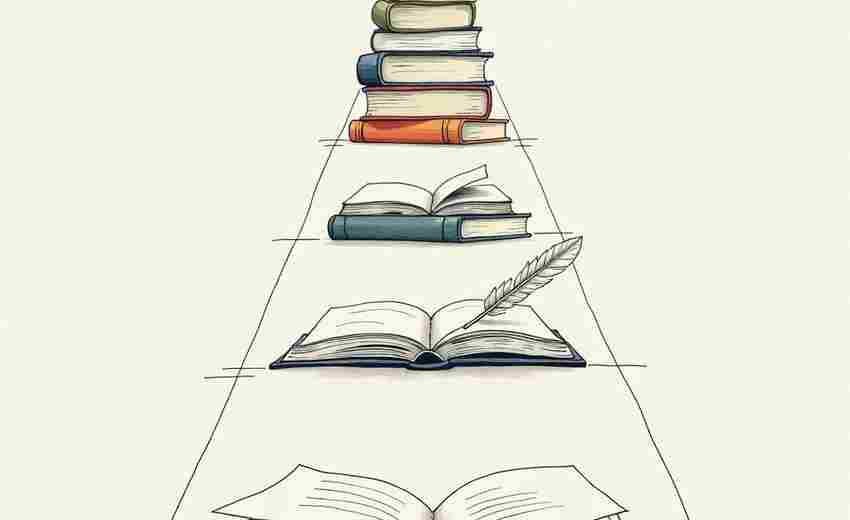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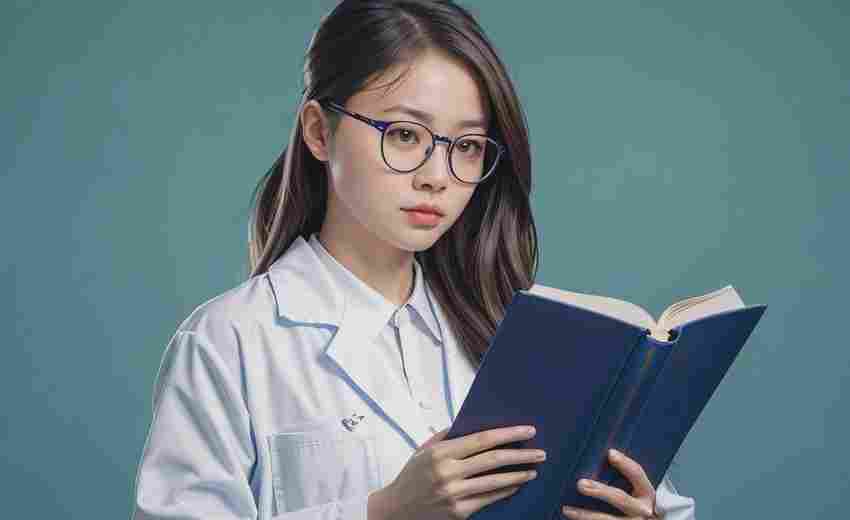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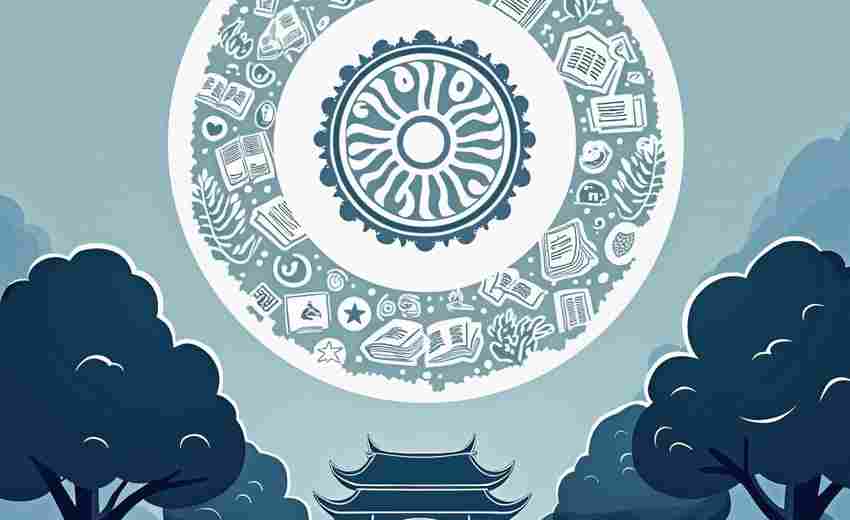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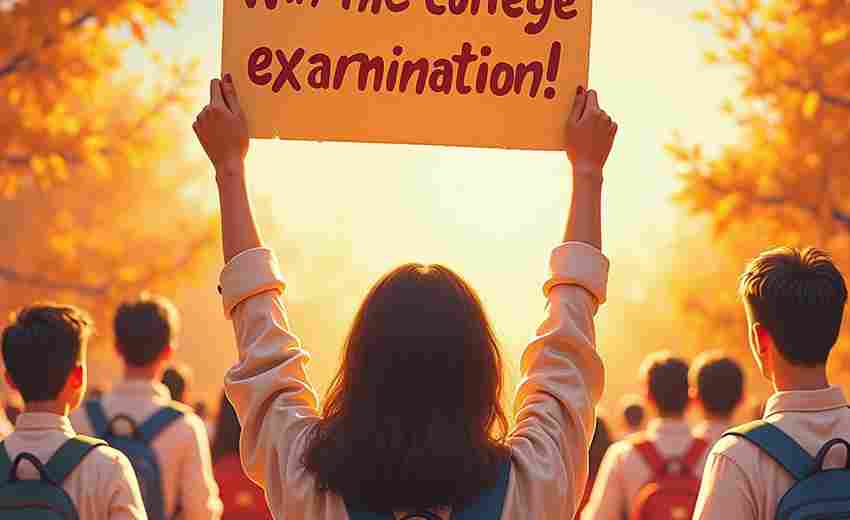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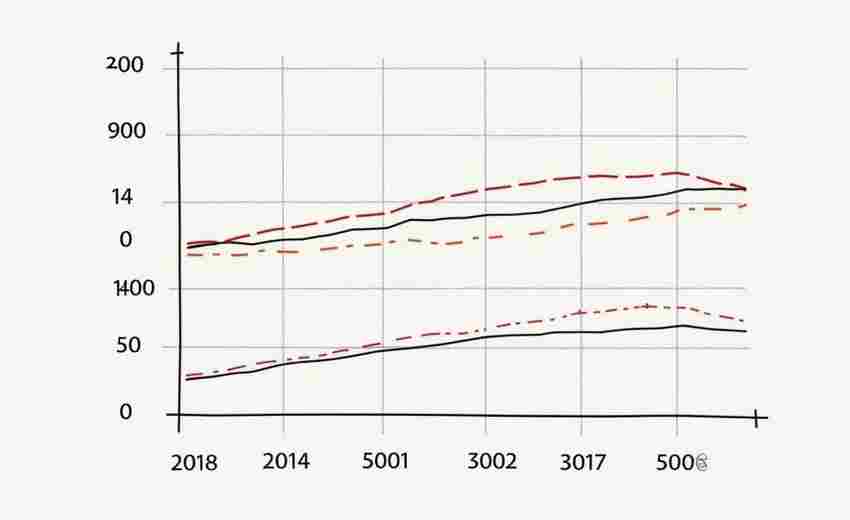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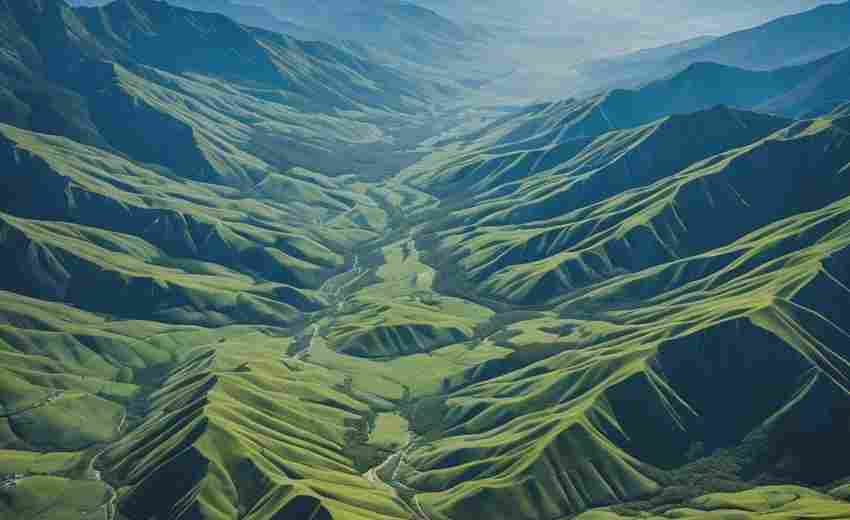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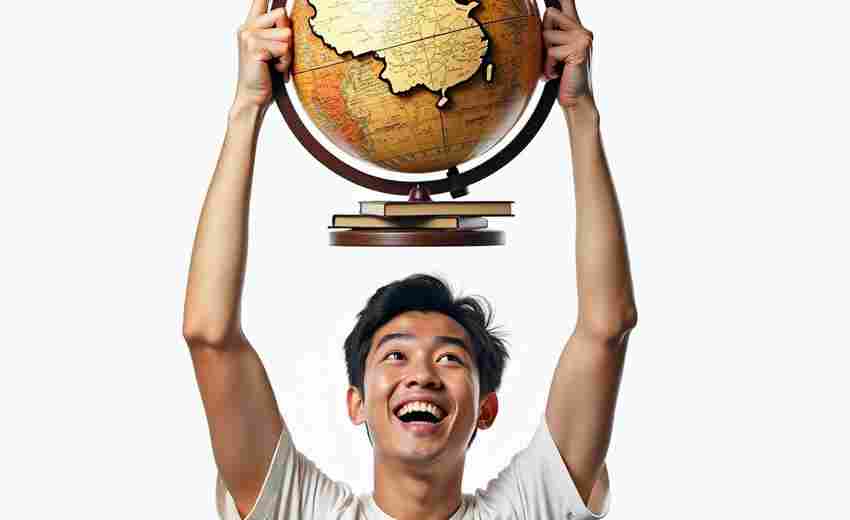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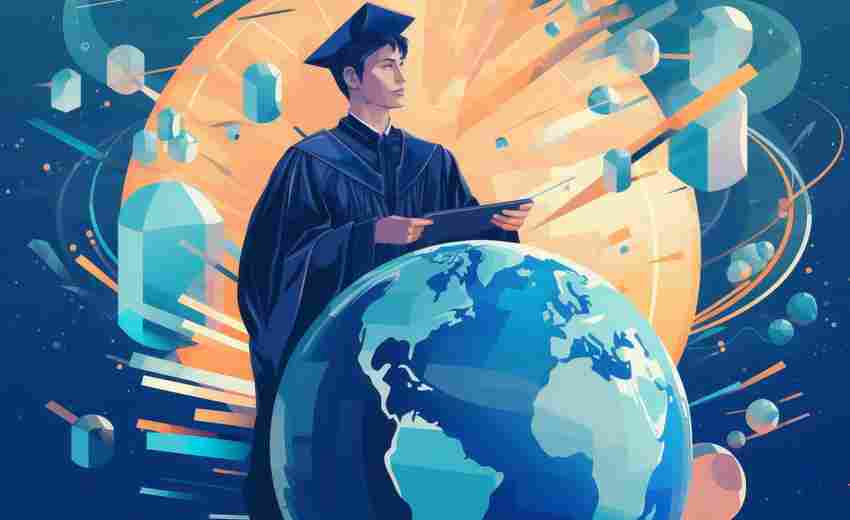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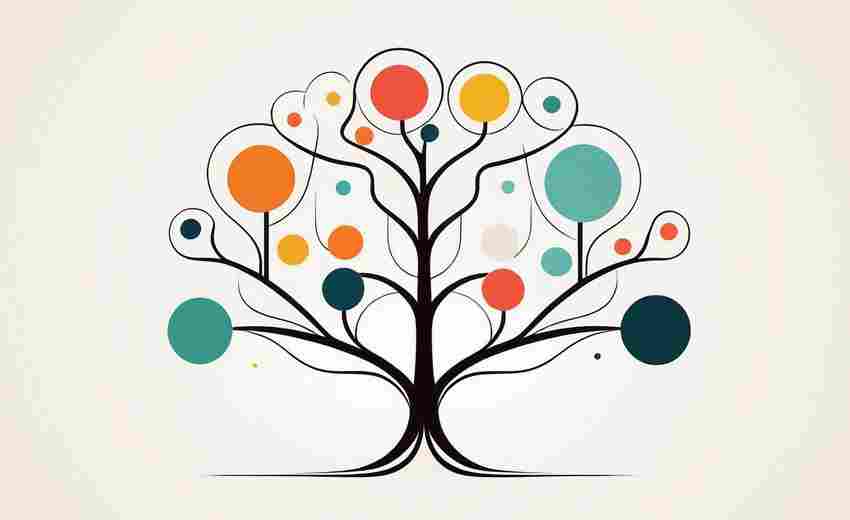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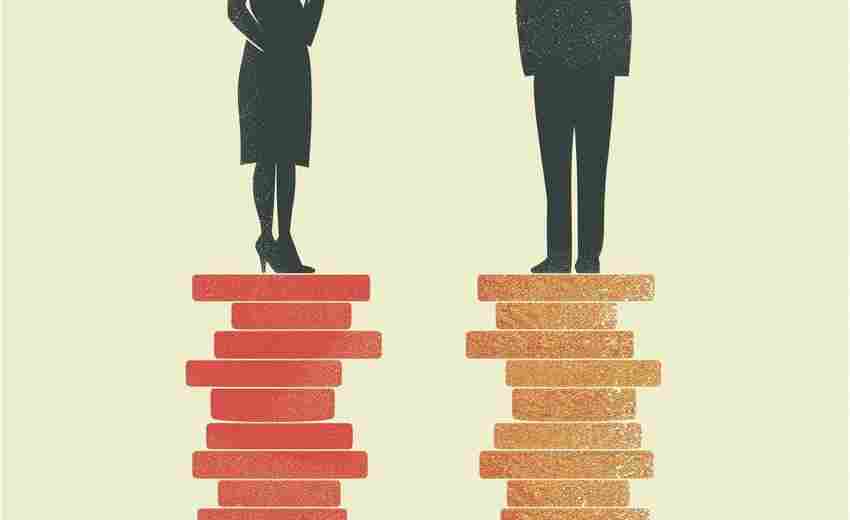





推荐文章
高考生如何通过影视公司实习提升专业认知水平
2025-06-17高考后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
2025-03-06高考志愿填报中如何有效倾听孩子的专业倾向
2025-08-22师范生参加社团活动的重要性
2024-12-15搜索引擎高级语法:精准定位高校招生简章的技巧
2025-08-16高考生必知:旅游管理专业主修课程与未来就业关联
2025-04-23数据科学热门技能中的编程能力在高考后如何提前准备
2025-07-10正切函数与正弦函数周期性差异在高考中的考点分析
2025-03-18高考照片人工审核需要携带哪些补充材料
2025-06-09语文基础知识薄弱点如何在一模前快速掌握
2025-06-25